防卫行为的整体性判断与时间过当概念之倡导
2021-06-07 16:48:34 5688次查看
转自:清华法学
作者:孙国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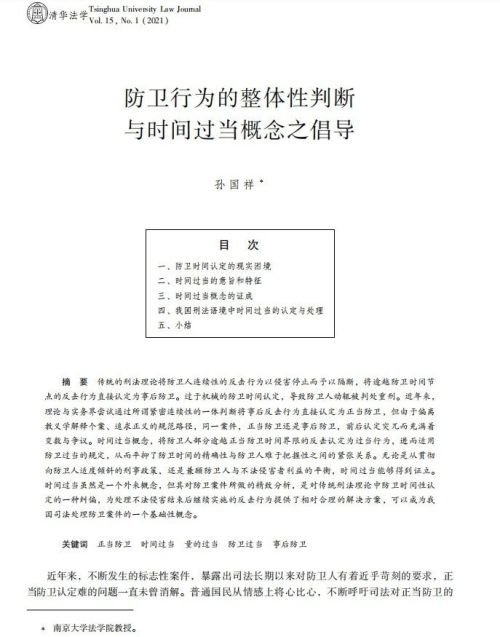
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标志性案件,暴露出司法长期以来对防卫人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正当防卫认定难的问题一直未曾消解。普通国民从情感上将心比心,不断呼吁司法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不能太“理性”,最高司法机关也强调处理防卫案件需要有正确的理念指导,并根据相关理念对热点案件作有利于防卫人的认定和指引。依靠网络舆情的影响机制,确实给于欢案、于海明案等案件的处理带来了转机。然而,热点沉寂以后,司法中防卫行为认定难仍是“涛声依旧”,刚被唤醒的正当防卫似乎又有再次“休眠”的迹象。因为理念固然重要,但理念毕竟不是规范本身,理念所形成的完全经验性的判断可能因个人喜好而裁判不一,缺乏稳定的预期。没有新的理论分析工具(概念)予以落实,再完美的理念在传统理论惯习面前充其量只能停留在应然层面,无法在实然的操作层面得到全面的贯彻。理念只有通过概念才有可能进入到规范层面,在规范化的框架内才能实现稳定的预期。本文所论及的时间过当概念,本是国外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开发的分析工具,其目的是为在不法侵害结束或者防卫效果发生后实施的连续性防卫行为如何处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这一概念可否移植到中国,移植后能够解决防卫案件认定中的哪些难题,是否与现有的分析工具(如防卫不适时、事后防卫)兼容,这是本文所研究的主旨。
理论和实务对刑法中正当防卫条件的解读和把握,最精确的恐怕莫过于防卫时间的节点。因为正当防卫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正在进行”被严格限定在不法侵害行为开始后以及不法侵害行为结束前这一点对点的时段内。对于尚未着手实施或者已经结束的不法侵害实施“防卫”行为,是防卫不适时,分别成立事前防卫或者事后防卫,不能作防卫性质的认定,如果行为人存在着认识上的错误,则按照认识错误处理,如果没有认识错误,则按照故意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时间认定,一直存在诟病,原因在于对防卫时间的要求过于严苛,留给防卫人的反应时间太短,导致极难构成正当防卫”。因为,正当防卫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将不法侵害是否开始或者是否结束分析得很精细,但在现实中也就是转瞬即逝的过程,要防卫人对不法侵害的开始和结束作出思前虑后的理性和符合规范的缜密判断,不啻是强人所难。防卫人出于防卫的意思实施了防卫行为,一旦不法侵害客观上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被认定为防卫不适时(事前防卫或者事后防卫),通常需要承担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人们“吐槽”正当防卫条款“休眠”,很大程度上源于司法对防卫时间严格把握,导致防卫人在行使防卫权时战战兢兢,不敢大胆地行使防卫权利,“立法设计正当防卫的初衷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撇开理论之争,梳理现有判决,涉及不法侵害事实上已经结束(或者不能肯定是否结束),对防卫人当场所进行的反击行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处理思路:
一是以防卫不适时(事后防卫)构成故意伤害(杀人)认定,至多认为被害人(不法侵害人)有过错而对被告人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例如,被害人张某打电话给被告人李某找其前妻但被李某拒绝后,张某随即威胁李某并乘出租车前往李某的住处。当晚9时许,张某来到李某的住处,不顾李某的警告,用脚踹开大门进入屋内,李某用长柄镰刀砍在张某的右额眉弓处。张某赶紧往外走,李某再次用镰刀砍在张某背上。案发后经法医鉴定,张某左面部的伤势为轻伤一级,后背的伤势为轻伤二级。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李某提起公诉,庭审中,李某和辩护人认为系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某对被害人张某的第二次挥砍是发生在被害人张某转身逃离过程中,此时不法侵害已经停止,张某对被告人李某的现实人身危险性已经解除,被告人李某此时将被害人张某砍伤不属于正当防卫,是防卫不适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该判决可以说是目前对类似的案件通常处理。
这种处理方式建立在立法上的正当防卫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基础上,侵害结束后实施的行为属于事后防卫。这是传统刑法理论思维当然结果。此种以时间节点将前后行为“一刀两断”的处理,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没有考虑防卫人的特殊境遇,没有考虑后行为是在前行为基础上趁势而为而形成的紧密联系。在一些案件中,不法侵害人的侵害客观上虽然已经结束,但侵害人仍在现场,防卫人处在受侵害和防卫的激奋之中,难于做出正确的判断,此种情况下,对不法侵害人连续性反击,其防卫性质能够得到人们情感上的普遍认同。这倒不是人们“以情废法”的“滥情”,而是人们朴素的正义感使然。因为“尽管法秩序要求,身处紧急防卫情形的防卫者尽管面临危险和困境,也要始终选择相对而言最为缓和的防卫手段,但这对于审慎的防卫者而言,已经是个难题了。如果行为人还出现了情绪冲动,那么丧失自制就再容易不过了。行为人身陷窘迫且多半扑朔迷离的情势这种弱势,使得他没能遵守紧急防卫的界限成为是可以理解、可以宽恕的事”。所以,这种处理尽管形式上合法,但既不合理,也不合情。
二是将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后出于防卫意思而实施的行为直接认定为正当防卫。多年来,理论界不乏放宽防卫时间界限的呼吁,主张将不法侵害结束的时间节点适当延后从而放宽防卫行为的时间限度。例如,有学者分析认为,不能将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侵害后果以及不法侵害人的退却一律视为不法侵害的结束。还有观点认为,“除非时空有明显距离,如对方已经逃走还长途穷追不舍等,否则不宜认定事后防卫”。这些呼吁尽管尚未成为指导司法实践的理论共识,不过确实也影响了对一些舆论“发酵”的热点案件处理。如著名的“涞源反杀案”。检察机关对该案审查查明,被害人王某因纠缠村民王新元之女被拒,某日晚11时许,持凶器翻墙闯入王新元家中,王新元在住房内见王某持凶器进入院中,并拿铁锹冲出住房,与王某打斗。随后,王新元妻子赵印芝持菜刀跑出住房加入打斗,打斗中,王新元和赵印芝被王某多处刺伤,构成轻伤和轻微伤。王某被打倒在地后两次欲起身。王新元、赵印芝担心其起身实施侵害,就连续先后用菜刀、木棍击打王某,直至王某不再动弹,王某最终失血性休克死亡。案发后,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新元、赵印芝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后,以王新元和赵印芝为使自己及家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暴力侵害,对深夜携凶器翻墙入宅行凶的王某,采取制止暴力侵害的防卫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遂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检察机关在对此案进一步释明中指出,本案案发时已是深夜,王某身材高大,年轻力壮,所持凶器足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虽被打倒在地,但还两次试图起身,王新元、赵印芝当时不能确定王某是否已被制伏,担心其再次实施不法侵害行为,又继续用菜刀、木棍击打王磊,与之前的防卫行为有紧密连续性,属于一体化的防卫行为。
将防卫人在侵害结束后的连续性反击行为前后整体评价,直接认定为正当防卫,其得出的不负刑事责任结论不但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似乎也符合司法“要根据常情常理考量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20年9月印发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本文以下简称为“两高一部”《指导意见》)也强调,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但分析的进路直接绕过了防卫时间性的评价,与正当防卫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规定相抵牾,有矫枉过正之嫌,缺乏说服力,尤其是对于为什么后来的击打行为一定是必要的,属于一体化的,缺乏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偏离教义学解释个案、追求正义的规范路径。例如,上例检察机关认定王新元、赵印芝的行为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防卫是可以接受的,但将其直接认定为一体化的正当防卫则显突兀。正如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从实务的层面来看,存在着将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进行混同从而不适当地扩大正当防卫制度适用。”
遗憾的是,此种混淆正通过一些典型案例不断强化。例如,某日凌晨4时许,李某夫妇在家中睡觉时被院内狗叫声吵醒,看见刘某(男,42岁)持尖刀刺其院门,并声称“劫道”。李某见状立即回院内取来一根铁管,并打电话通知村治保主任等人前来帮忙。刘某来到李某家厨房外,用尖刀割开厨房纱窗,被李某妻子发现后躲进了院内玉米地。李某持铁管进玉米地寻找刘某,在玉米地与持尖刀的刘某相遇,二人发生打斗。李某持铁管击打刘某头部,致刘某颅脑损伤,次日死亡。公诉机关指控李某构成故意伤害罪。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的行为系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诉机关认为被害人躲进玉米地后,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已经消失,因此,李某的行为不具有防卫的性质,遂提起抗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被李某妻子发现后躲入院内的玉米地,虽未继续行凶,但其躲避的目的是准备逃避现场还是伺机行凶,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明。同时,在案证据证实刘某患有精神病,案发时处于精神异常状态,攻击他人的可能性较大。刘某躲在玉米地内对李家人仍有现实威胁,也可认为是侵害状态的延续,故认为被害人躲入玉米地后不法侵害仍然存在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二审遂维持李某行为系正当防卫的原判。二审的裁判逻辑是建立在刘某躲入玉米地是继续行凶还是躲避无法查明,有伺机行凶的可能性基础上的。“两高一部”《指导意见》也规定,“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但问题是,所谓“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如何判断,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一种猜测。防卫时间性的判断应该是客观的,不应该以防卫人的主观认识为转移。易言之,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应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更不能因为遭受了不法侵害就忽视了防卫人可能存在的错误判断。如果这样的话,那在刑法理论中也就不存在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的概念了。
由此可见,两种处理方式各执一端,要么是普通的故意犯罪,要么是不负刑事责任的正当防卫,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逾越防卫的时间界限,要么就是判处重刑的“阶下囚”,要么渲染成为同犯罪作斗争的“英雄”,前者不能彰显司法应该向防卫人倾斜的刑事政策要求;而后者也可能向社会传递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即防卫的时间已经是无关紧要。因此,司法实践客观上亟需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将两个极端予以平抑。本文认为,这样的工具可能是现成的,时间过当的概念或许能够担当起这一责任。
在比较法的视野中,防卫行为的时间界限是各国刑事司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对逾越防卫时间界限的行为如何处理也会产生同样的困惑。立法和理论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存在着不同的路径选择。在比较中,时间过当的提出和运用,逐渐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
在英美法系,虽然通说也强调,“合理的自我防卫必须既不能过迟也不能过早”。但在司法把握上,以防卫人为中心,站在防卫人的立场上,只要防卫人有理由相信他遇到了不法侵害就可以防卫。法律允许行为人实施防卫行为在防卫人认为合理的情况下使用,而不问这种判断合理与否。换句话说,不管客观上是否存在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是否结束、是否有必要予以防卫,防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只要防卫人合理相信其反击行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就成立正当防卫的合法辩护。这种主观主义的立场赋予了司法对防卫时间的极大的裁量权,将防卫时间的客观判断置换为防卫人的主观认识,并不妥当。
在大陆法系,防卫时间性的判断一直秉承客观主义的立场,强调正当防卫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侵害行为。而为了缓解时间性的精确认定与防卫人无法精确把握的矛盾,一些学者尝试将逾越时间的反击行为作为防卫过当处理。晚近以来,德日刑法学界正当防卫理论的重要发展之一,就是对防卫过当进行类型性的划分,普遍地将防卫过当的类型分为强度过当和时间过当两种情况。前者是指“在急迫不正的侵害继续进行中所实施的防卫行为本身超过了必要限度”;后者是指“侵害结束后又实施了反击行为”。在日本刑法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将强度过当称之为质的过当、手段过当,将时间过当称之为量的过当或者事后过当。我国学者大都沿用日本学者质的过当和量的过当之称谓。本文无意比较不同名称的差异,只是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质的过当和量的过当过于抽象,质的过当(程度过当)某种意义上也是量的过当,该理论融入中国的语境中,恐怕用强度过当和时间过当更能体现中国的语言习惯和意旨。
时间过当的概念提出后,也曾受到传统理论的责难。一些学者坚持防卫行为必须是在不法侵害的正在进行时才能实施,不存在时间过当的空间。例如,日本有学者坚持认为,“客观上侵害已经结束的时点,只能认为正当防卫状况已消失,此时认定防卫过当的成立是困难的。与其将此种情形的量的过当作为防卫过当来处理,不如将其作为误想防卫或误想防卫过当的问题来处理……只要侵害的继续性不被认定,则就不能作为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来处理”。意大利学者也认为,“在危险过去后才实施的行为可称为反击,但不是防卫”。匈牙利刑法学者虽然接受时间过当的概念,但认为,“与防卫过当相关的条款只与正当防卫情境下发生的活动相关,却无关时间过当的问题”。
然而,时间过当的基本精神,就是在防卫人在连续实施数个防卫行为的场合,由于数个防卫行为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连续的,因此,应该将数个行为作为一系列、一体化的行为来评价并在整体上肯定防卫过当。防卫人据此也就享有依照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可能,从而缓解了防卫时间认定上的精确性与防卫人现实中难于把握的紧张关系,不失为一种具有深受启发性的折中和妥当的解决方案,其不言而喻的合理性使其迅速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
时间过当的概念是建立在防卫行为整体评价基础上的,那么,基于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将逾越防卫时间界限的反击行为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所实施的防卫行为作一体性的评价呢?通常,作为整体评价的时间过当体现在主客观两个方面的特征上。
1.客观上,防卫人对不法侵害者实施了数个反击行为,数个反击行为具有连续性。这是时间过当成立的客观基础。详言之,时间过当在具有以下客观特征:
(1)防卫人确实遇到了已经发生的不法侵害。德国学者强调,时间过当之所以能够证立,很重要的原因是,“过迟的‘量的防卫过当’的情况下,已经存在过(可以解释受攻击者也就是其后的防卫过当行为人的反应的)紧急防卫情形,只是这种紧急防卫情形在时间上‘过时’了”。防卫人可能在侵害行为进行时已经实施过防卫行为,也可能在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后才开始实施反击行为,但无论如何,不法侵害确实已经发生。对尚未开始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广义上也称之为时间过当,但一般认为不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理论上对时间过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过迟的反击行为的性质上。
(2)防卫人一般实施有数个反击行为。所谓数个反击行为,是从行为的自然属性角度予以观察,防卫行为可以作复数认定。例如,甲用拳击打乙,乙一拳将甲击倒,又顺势用力踢了乙一脚,甲被踢成重伤。防卫人的一拳一脚可以被认为前后实施了两个反击行为。而倘若甲侵害乙,乙反击将甲摔倒,甲抓住一根棍子欲爬起继续实施侵害,乙遂扑上去压住甲并用双手卡住甲的脖子,甲开始挣扎,后渐渐停止,甲被掐后窒息死亡。乙卡住甲的脖子是一个行为的连续过程,无法进行分解,只是一个行为,因而只有可能存在着强度过当,而没有时间过当的存在余地。不过,本文认为,在不法侵害进行时未能及时实施防卫,不法侵害结束后随即反击的,即使只有一个单数行为,也不排除作时间过当认定。如甲男对乙女实施强奸,乙女在甲男得逞穿裤子欲离开之际,趁势抓起菜刀砍向甲男头部,致甲男重伤。乙女的行为也应属于时间过当范畴。
(3)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或者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已经实现了防卫的效果(制止了不法侵害)。时间过当不是建立在侵害行为持续性基础上的,如果能够肯定侵害行为在持续进行中,实施的防卫行为就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不过,不法侵害是否结束或者防卫行为是否已经实现了防卫效果,在具体案件中不无争议。本文认为,是否结束应该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作判断,不能以防卫人的主观认识为依据。客观依据通常包括不法侵害人已经被制服、侵害人实施了逃避行为以及不法侵害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不能继续下去等情形。
(4)反击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具有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当场性。尤其是在复数反击行为的情况下,后行为具有前行为趁势而行的特点。也就是说,前后行为存在时间上的直接联系,“根据这种联系,人们可以将防卫行为及其后续部分自然地看成一个整体的事实发生过程”。不法侵害结束后的反击行为,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连续不间断的反击行为,其中部分行为是防卫目的实现后的行为。或者说,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后,已经不存在持续的现时攻击,而防卫人继续反击,这样就从时间上逾越了容许的紧急防卫的界限,在持续时间上越界了。例如,防卫人一拳将不法侵害人击倒在地,不法侵害人客观上已经身负重伤,无力再实施不法侵害,但防卫人仍然向不法侵害人的腹部猛踢一脚,这一脚属于侵害结束后的行为。二是追击行为。防卫人实施反击行为后,不法侵害人退缩,防卫人趁势追击,继续击打不法侵害人,即使离开了一开始不法侵害的现场,但从现场始发不间断的追击所到的地方,可以视作案发现场的延续。
2.主观上,防卫人的数个行为具有防卫意思的连续性。防卫的认识,是指防卫人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在时间过当的场合,前后行为都是出于防卫的意思而实施。如果后行为不是出于防卫的意思而是基于报复、泄愤等目的而实施的,则不能作防卫行为的认定。防卫人主观上的防卫意识存在着以下两种情况:
(1)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但防卫人误认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并在防卫意识支配下继续实施反击行为。也就是说,防卫人的行为仍然是在防卫意识支配下实施的行为。“两高一部”《指导意见》提出,“对于防卫人因为恐慌、紧张等心理,对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产生错误认识的,应当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依法作出妥当处理”。何谓“妥当处理”,《指导意见》对此本身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如将此种行为统一纳入时间过当范畴中,则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解决方案。
(2)不法侵害的攻击行为已经结束,防卫人对此亦存在认识,但由于过度的恐怖感与心理上的动摇,而防止再次攻击而继续实施反击行为,典型的就是继续追击的行为。严格意义上,防卫人既然已经认识到不法侵害行为的攻击行为已经结束,其后实施的反击行为就不属于基于防卫意思而实施。不过,日本学者分析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为人虽然认识到侵害已经结束,但由于过于兴奋或者狼狈,出于对方说不定还会再次攻击这种不安之中,从而实施了追击行为的,如果认定为“完全的犯罪”,对行为人而言,这种结论未免过于残酷;由此,“虽然要求的是防卫意识的连续,对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也并非要求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防卫意思(认识到侵害,并试图排除该侵害的意思),只要能认定,与侵害持续性过程中的对抗行为的主观方面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即已足够”。换句话说,时间过当的情况下,并不要求明确的防卫意思,只要没有明显表现出积极的报复行为,就可以作防卫意思的连续性认定。
对时间过当的肯定,必然涉及其与事后防卫的关系,毕竟两个概念有太多的共同元素。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时间过当通过防卫意识以及数个反击行为的连续性一定程度扩张了防卫行为的认定,限缩了事后防卫的成立范围。只要在不法侵害和防卫行为实施的现场,防卫人基于防卫意识所进行的多个反击行为,大概率可以认定为整体性的防卫行为。不过,对时间过当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否定事后防卫概念的意义,更不意味着凡防卫人的事后反击行为,都可以作防卫过当认定。如果这样,无疑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事后防卫就是时间过当。虽然时间过当的本意是扩大防卫过当的范围,但也只是从传统的事后防卫中分离出一部分连续性的反击行为,并不否定事后防卫的存在。时间过当的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出于制止不法侵害人进一步的侵害行为所实施,具有“风险预防措施”的性质,而事后防卫则代行了国家本应由对不法侵害人的回应。例如,甲挥拳侵害乙,乙反击,连续几拳将甲打得跪地求饶,乙仍不解气,又对甲连踹几脚,将甲踹成重伤。既然甲客观上已经跪地求饶,乙的连踹几脚的行为主观上并非出于防卫的意思,不具有防卫性,应属于典型的事后防卫,不能作整体性的防卫行为评价。
时间过当之所以能够成为普遍接受的概念,不但因为其缓解了防卫时间的精确性要求与防卫人难于把握性的现实形成的紧张关系,具有实践优势,而且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论证成。
不少学者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论证,时间过当本来就应该属于防卫过当的一部分。
首先,从形式上看,虽然人们通常理解的防卫过当是强度的过当,但事实上,刑法规定的防卫过当并没有限定为强度的过当。在德国,学者针对如何理解德国刑法中“紧急防卫的界限” 时指出,“条款中‘紧急防卫的界限’也可以理解成为时间上的界限。此外,由于在动机情况上没有什么区别,因而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将之和‘质的紧急防卫’区别对待”。时间过当,实际上表述的是一种客观现象,“如果早些时候真的存在过正当防卫的情景,但是不法侵害或以不法侵害构成的直接威胁已经结束之后,防卫者仍然在之前的不法侵害影响下(比如因为受情绪影响)继续行动的话,也可判定其为时间过当”。对此,我国学者也分析认为,时间过当完全可以涵括在我国刑法的防卫过当范围中。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其中的“必要限度”并没有局限于防卫强度与防卫结果的限度条件,完全可以包括时间限度,这在文理解释上没有障碍。
其次,形式的解释能够得到实质解释的支持。过于形式的解释难免诟病为牵强附会,但如果一个形式的解释能得到实质解释的印证,逻辑上也就基本上实现了自洽。时间过当倡导者分析认为,时间过当与强度过当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理应享有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优惠”。如德国罗克辛教授分析认为,一个人是以超过必要限度1倍的力度进行防卫(强度过当),还是在一次符合必要限度的防卫制止了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又进行了第二次同等力度的打击(时间过当),这在刑事政策方面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设想防卫人使用的是同等的力量,那么,两次有节制的打击,比一次无节制的过分的打击来说,其危害性要小,更值得原谅。从不法的程度上看,“当一个人在一种有节制的反应中轻微地超越了紧急防卫的时间界限时,与他在一种目前的攻击中严重超越了必要性的界限相比较,他的不法就能够轻微得多”。我国有论者也有同样的分析:“从司法实践来看,虽然一般也会对事后防卫从轻处罚,但同样是在一个行为过程中,防卫行为如果发生在不法侵害过程中‘应当减免处罚’,而发生在不法侵害过程外,则只能‘酌情从轻处罚’,是否妥当?”本文看来,这些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例如,甲遇到小偷入室盗窃,防卫人用刀猛刺一刀,致小偷死亡,是强度过当。而乙遇到小偷,用拳猛击小偷,小偷转身逃跑时,乙又趁势上去猛踢一脚,致小偷重伤。此种情况,前者作为防卫过当认定没有异议,防卫人享有减免处罚的“优惠”;后者如果不认定防卫过当,直接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比前者造成死亡还要判的重,罪刑明显失衡。如果认定为时间过当并按照防卫过当处理,能够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并且,将此种行为按照事后防卫进而以普通的故意犯罪定罪量刑,常常导致情法尖锐对立,如对“昆山反杀案”一边倒的舆情就是人们情理的自然反应。
(二)时间过当作为防卫过当,符合防卫过当的减免处罚的实质根据
将时间过当作为防卫过当处理,能否从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实质根据中推导出时间过当作为防卫过当认定的合理性,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换句话说,时间过当既没有逾越刑法关于防卫过当的范围,也没有悖离刑法关于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规定。张明楷教授指出:“量的过当具备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实质根据。”何谓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实质根据,一般认为,“防卫过当的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动机是出于正当防卫,其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也小于其他故意犯罪”。这一理由较为抽象,主观恶性较小容易理解,但社会危害小于其他故意犯罪则含混不清。
在日本和德国刑法学界,学者围绕着防卫过当减免刑罚的依据,有“责任减少说”“违法减少说”和“违法责任减少说”之争。责任减少说认为,防卫过当之所以可以减免处罚,是因为考虑到“行为人在遭受对方攻击的紧急状态、在法益冲突状况这一紧急状态之下,因恐怖、惊愕、兴奋、狼狈等心理动摇而减少了期待可能性,因而才肯定具有减免刑罚的可能性”。以此观点,“防卫过当不是违法阻却原因,而是责任阻却原因”。违法减少说认为,“虽然防卫过当没有完全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但与单纯的法益侵害行为不同,是面向不正侵害的防卫行为;既然如此,违法性有所减少”。违法责任减少说认为,“防卫过当,在其属于针对急迫不法的侵害的防卫行为这一点上,较之并非如此的单纯法益侵害行为来说,必须肯定其违法性的减少;但是,要想说明防卫过当就连刑之免除也是可能的,就必须考虑心理的压迫状态所导致的责任的减少”。也就是说,防卫过当,既是责任减免事由,也是违法减免事由。这是目前多数学者的主张。
本文认为,传统的防卫过当指的是强度过当,是正对不正的过程中发生的,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无疑是不正的,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有正一面,也有不正的成分(强度过当那部分),尽管出现了一个过当的结果,因为存在着正的成分,所以不法的量减少了。由于防卫过当是在防卫过程中形成的,防卫人心理上伴随着恐惧、惊愕,责任相对也减轻了。因此,违法和责任减少说是合理的。
不过,时间过当,是在不法侵害结束后实施的,并不具有正的成分。由此,时间过当是否也存在着违法性的减轻?罗克辛教授持肯定态度,认为当一个人在一种有节制的反应中只是轻微超越了正当防卫的时间界限时,与其在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防卫中严重超越了必要性的界限相比较,他的不法实际上是轻微得多。在本文看来,时间过当的情况下之所以不法程度降低,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侵害人的侵害本来具有自招风险的性质。德国学者举例认为,在不法侵害结束后,防卫人因为慌乱、恐惧或者惊吓而逾越了防卫的时间界限,但却误击了无辜的第三人,对此,因为无辜的第三人不需要为防卫人的惊慌失措承担责任,所以防卫人的行为并没有减轻不法,故不能适用德国刑法典第33条防卫过当的免责事由,而只有在防卫人在受到不法侵害者侵害后精神上出现慌乱、恐惧或者惊吓,不法侵害者“要对引发情绪冲动的情形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时间过当所针对的对象的特殊性(不法侵害人),所涉及的是不法侵害者的权利空间,使得行为的不法程度有所减轻。对此,我国有学者也有分析:“从法秩序的维护来说,当犯罪分子置法律秩序于不顾挑起不法侵害时,他不仅是将受害人置于了不受法律保护的境地,同时也是将他自己置于了不受法律保护的境地,而当他在自己所一手造成的状态中沦为对方‘事后’防卫行为的‘受害人’时,这样的‘受害者’是不应当获得相应的法律保护的,这就是普通人所说的‘活该’。”不同的表述意思都差不多,不法侵害者的攻击给自己带来了风险,由此保护的必要性降低了。第二,不法虽然是规范评价,但不法程度的评价需要考量的因素要广泛得多。时间过当的情况下,公众对防卫人的逾越时间的防卫行为普遍有一定的容忍度,由此,也带来了不法程度的降低。
因此,时间过当同样存在着不法减少和责任减轻的情况。具备防卫过当减免处罚“优惠”的实质根据。
时间过当概念,既是对司法裁判放宽防卫行为时间限度刑事政策的一种理论抽象,也成为指导司法裁判的重要分析工具。
首先,时间过当适当扩大了防卫过当的认定范围,回应了有利于防卫人的刑事政策精神。对防卫限度的判断,应向防卫人倾斜已然成为社会的共识,也是现阶段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但司法中的刑事政策贯彻终究不能脱逸刑法本身的规定。向防卫人倾斜,只能是在遵守而不是要颠覆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基本条件的框架内实现。时间过当概念,较好地平衡了贯彻刑事政策与执行刑法、情与法的关系。将时间过当纳入防卫过当的范围,“一方面,可以通过将时空上具有连续性的防卫行为一体评价,将理论上被作为犯罪处理的防卫不适时的事后防卫与其前面的正当防卫一体评价为防卫过当,从而整体上缓和事后防卫的违法性色彩;另一方面,为事后防卫享受日本刑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的减免处罚的优遇提供便利。毕竟事后防卫,很大程度上是由被害人的紧急不法侵害行为所引致的,行为人在责任上具有可以宽恕或者理解的一面,即便其因为防卫不适时而成立犯罪,但在处罚上也必须与一般犯罪区分开来”。易言之,适当扩大防卫过当的范围。“对于趁势继续实施了追击行为的情形,认定为完全的犯罪,对行为人而言,过于残酷,因此,对于那些可以与侵害当时的对抗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的案件,通过承认就整体行为成立防卫过当,给予被告人以减免刑罚的可能性。”
其次,对逾越时间界限的反击行为作时间过当认定,否定了不法侵害人对该反击行为的防卫权。实际上,此种情况如果不做防卫行为的认定,将其认定为一个普通的事后防卫的犯罪,也就无法否认不法侵害人对该反击享有防卫权甚至享有特殊防卫权,这不但可能给最初的防卫人以二次伤害甚至更严重的伤害,而且也是普通民众的法感情难于接受的。肯定持续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不法侵害人实施侵害行为的时候,应该承担该侵害行为带来的可能的连续性反击行为,这也就否定了“自作孽”的不法侵害人的防卫权。如受到追击的不法侵害人不能借口人身权利受到威胁而实施所谓的“防卫”。
再则,兼顾了被害人(不法侵害人)的利益。不法侵害人在停止侵害或者逃匿的过程中,其不法侵害过程中失去的法益保护需要性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果将防卫人在侵害行为停止或者逃避后继续击打或者追击行为作为完全的正当防卫行为认定,则将侵害人置于完全不受保护的境地,导致防卫人可能毫无顾忌地追击,法益保护也会失去平衡。时间过当,虽然肯定防卫人继续击打和追击行为的防卫性质,在时间过当的框架下,由于并没有否定相反仍坚持了《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一防卫时间性要求,对逾越时间界限的防卫仍然是不被允许的,不法侵害结束后的反击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正当防卫行为,而是归属于需要承担责任的过当范畴,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仍需要秉持一定程度的谨慎,只是视情况减免处罚。换句话说,尽管侵害人的法益保护必要性基于自己发动的侵害行为而降低,但并没有完全丧失,通过时间过当的评价和减免责任使利益保护相对平衡。
(四)有助于厘清正当防卫、防卫过当与事后防卫之间的界限
如前所述,从实务来看,现阶段司法对于不法侵害停止后防卫人进一步的反击行为,在认定上进退失据。大多数案件作为防卫不适时的事后防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乃至故意杀人罪。不少学者热衷于通过对不法侵害的“正在进行”的时间性滞后,寻找将事后防卫正当化路径。尽管初衷是对机械认定防卫时间性的纠偏,结果也似乎符合民众的期待,但颠覆了传统刑法理论对防卫时间性的精确界定,具有扩张正当防卫范围的意旨,同时混淆了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的界限。而且,人为将“正在进行”这一客观的时间性标准滞后,无疑将防卫时间的客观判断与防卫人的主观责任要素(主观上有没有认识到不法侵害结束以及是否因为恐惧和紧张的精神状态而缺乏期待可能性)混为一谈,逻辑上难于自圆其说。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现在性’问题乃做为正当防卫前提条件的正当防卫状况之问题,因此该前提状况是否存在,应以纯粹外在的、客观的情事加以判断,而不应受防卫者之主观意思所左右”。时间过当,在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之间设置了一个过渡的桥梁。
一旦肯定时间过当的概念,那么,时间过当与事后防卫应该是互斥的,不能混淆。中国法院裁判文书网上一份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上诉人拳击被害人致被害人轻伤,其行为虽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不适时,不构成正当防卫”。判决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肯定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又只是造成轻伤,即使超过必要限度,也应该认定为正当防卫。如果肯定被告人防卫不适时,那就不具有防卫的性质,也就不能成立防卫过当。总之,防卫性质与防卫不适时无法同时证成,一旦认定事后防卫,就无法认定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时间过当概念在防卫时间性认定上所具有的优势,在一些文章中提出引进和提倡时间过当概念。例如,张明楷教授就提出,我国应当借鉴日本判例与通说的观点,将事后过当认定为防卫过当。防卫人基于一个行为意志发动的防卫行为,只要在时间上、场所上具有持续性、一体性,就可以评价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而不应当进行人为的分割。而对于时间过当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不是只能免除处罚,而是也可能减轻处罚,因而也可以做到量刑适当。付立庆教授进一步指出,“量的过当”的概念,一则可以将不法侵害结束前后的一连串行为规范地评价为一个整体,二则在高度紧张、恐惧或亢奋的状态之下,要求受到不法侵害者明确地判断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以确定是否可以继续自己的反击行为也属强人所难。因此,接受“量的过当”的概念,肯定侵害行为终了前后的一连串行为整体评价,肯定终了后的行为即使构成犯罪,也属于防卫过当,是一种务实的选择。
但总体上看,时间过当仍然被我国学界忽视。对时间过当概念的忽视(否定)一方面源于传统事后防卫概念的坚守。在传统刑法理论上,只要是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即使防卫人出于认识错误而实施防卫行为,也属于事后防卫,应根据行为人主观方面故意或者过失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各国正当防卫制度对防卫过当的处理毕竟有诸多差异,即使是德日刑法学界普遍肯定时间过当概念,他们的实务界则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日本,防卫一旦过当,尽管可以减免处罚,但不问过当结果如何,原则上都能成立犯罪(如暴行罪)。但在德国,对防卫过当的责任追究本来就十分宽容,《德国刑法》第33条规定,“防卫人由于慌乱、恐惧、惊吓而防卫过当的,不负刑事责任”。故实务中对防卫过当的把握谨慎,对时间过当持排斥的态度,毕竟一旦承认时间过当,“对量的防卫过当也一概不予处罚,可能并不合适”。不过,即使在德国,时间过当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已经显现,为了回应理论界扩展防卫时间界限的主张,德国司法判决将“攻击的当前面临性”(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扩张为“最终排除攻击危险”,防卫人“即使仅仅应当担心,那个本身已经被击退的攻击随后很快就会再回来,那么,‘当前面临性’就应当还存在,因此,在这个阶段的紧急防卫超过限度就可以判断为集中的超过限度了”,罗克辛教授因此认为判例实际上已经接近于承认“扩展的超过限度”(时间过当)了。
本文虽然主张我国刑事司法中应当倡导时间过当的概念,但同时认为,各国防卫过当制度的差异,时间过当的具体运用也有所不同。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规定有自己的特色,在引进时间过当概念时,不能采取完全“拿来主义”的立场,而主要是借鉴其基本精神,结合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作具体分析。
在肯定时间过当概念基础上,如何确定一个时间过当行为该当了刑法上的防卫过当,理论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规则。时间过当,实际上涉及连续实施的行为防卫性质的认定以及连续实施的行为具有过当结果认定两部分内容。过当结果是由连续实施的行为整体性造成的,还是连续性行为中逾越时间性的“过迟”行为造成的,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如前所述,在日本刑法中,因为有暴行罪的规定,“过迟”行为无论是否造成具体的结果,都具有暴行罪的该当性,评价指向的基本上是过当行为本身,因而是整体判断还是分别评价都不太会影响时间过当该当防卫过当。我国刑法不但没有暴行罪的规定,而且《刑法》第20条规定,只有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造成了重大损害,即只有在行为过当与结果过当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具有防卫过当的该当性。本文认为,基于我国刑法对防卫过当的特殊规定,时间过当是否属于防卫过当,应循着防卫性质的整体判断与过当结果分别认定相结合的步骤进行分析。
1.对过当行为的防卫性质作整体性的判断。防卫性质的认定是建立在前后行为连续性基础上,而连续性的认定也是建立在主客观基础上。主观上,防卫人的防卫意识具有连续性。之所以作防卫过当的认定,首先是因为防卫人的防卫意思并没有结束,其认为有进一步进行防卫的必要。这基本是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即在防卫意思持续范围内的行为应被赋予防卫行为的意义和性质。“即使是在从自然角度来观察发现存在复数行为的情形中,只要复数行为由同一防卫意思承担,就能够将这些复数行为作为‘一系列防卫行为’来把握。”但仅凭防卫意思的连续性,还不足以认定行为的防卫性质,因为事后的假想防卫,同样可能具有防卫意思。所以,还必须从客观上分析,防卫行为是否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客观上的这种连续性,通过现场的时间的接续性、现场的同一性以及后行为是前行为的趁势而为得以反映,某种意义上,连续性的反击实际上是防卫行为的自然延伸。例如,前文提到的“涞源反杀案”,王某实施不法侵害,王新元、赵印芝将王某打倒在地,结合案发时现场情境以及王某倒地后仍有两次起身动作等因素,在王某倒地后因担心王某继续侵害而连续击打,该行为逾越了防卫的时间界限。但后续的击打行为是出于防卫的意思,后续的击打行为与之前的行为确实有紧密连续性,应属于一体化的防卫行为,检察机关对该行为属于防卫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属于时间过当。又如,于海明防卫案中,于海明对不法侵害人刘某连续捅刺和砍击有7刀,其中5刀是在不法侵害人刘某实施侵害过程中,砍刀脱手,于海明夺得砍刀,刘某上前抢砍刀的过程中实施的,其防卫性质在讨论中没有争议。后两刀是刘某受伤后朝其停车的位置走,于海明在追击过程中实施的(未砍中),对于这两刀的性质,高检院的分析意见指出,“刘某受伤后又立刻跑向之前藏匿砍刀的汽车,于海明此时作不间断的追击也符合防卫的需要”。什么是防卫的需要,这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防卫的需要是制止不法侵害,如何确定刘海龙还继续实施不法侵害并需要通过防卫予以制止呢?有观点分析说,“即使刘某已经退逃,也不能简单认定刘某彻底打消了侵害的意图。事实上,刘某龙在与于海明发生口角的时候,就反身走到宝马车边,从车里抽出砍刀,而在防卫人夺刀之后刘某退逃的方向也是宝马车的方向”。言下之意,刘某有可能会去拿刀拿枪继续对于海明实施侵害。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揣测,“正在进行”是经过确证的客观事实,而非揣测的可能性。所以说,后面的两次砍击并不符合防卫的时间性要求,逾越了防卫的时间界限。但这2刀与前面的5刀(追击中的两刀)紧密相接,应作一体化的防卫行为认定,进而排除事后防卫的性质,将后面的两次砍击评价为时间过当比较妥当。
2.防卫行为是否过当需将前后行为分别评价。在行为防卫性质的整体性评价基础上,对一个时间过当的案件,如何进一步判断已经该当了刑法上的防卫过当,同样存在着整体判断和分别判断两种路径。整体判断,是指将前后防卫行为以及造成的结果统一判断,得出其行为和结果是否过当的结论。“在逾越时间限度的事后防卫中,也没有理由将防卫行为割裂开来判断,不管是在质的防卫过当中,还是在量的防卫过当中,都应当采取整体性判断方法。”在日本,最高裁判所通过判例肯定了对防卫行为的整体性评价。该案的大致案情如下:在拘留所内,被告人甲被被害人乙用折叠桌推倒,被告人甲实施了将该折叠桌推回的暴力(第一暴力),之后,对于撞上折叠桌而摔倒、处于难以反击的状态之下的被害人乙,继续数次击打其面部(第二暴力),但只有第一暴力与被害人乙的伤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并且,若单独评第一暴力,完全存在满足防卫行为之相对性的可能。对此,最高裁判所判定,在上述事实关系下,被告人对被害人施加的暴力,属于针对紧迫的非法侵害行为而实施的一系列、一个整体的暴力,能认定基于同一防卫意思的一个行为,因此,进行整体性考察,认定成立防卫过当是的伤害罪是相当的。日本学者质疑认为,由于造成死因的第一暴力可以评价为正当防卫,第二暴力,防卫意思在继续,整体评价毋宁说本应从轻处罚的案件,反而处断更重。我国学者也有同样的担心,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之时,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是法律所允许的,在必要限度内实施防卫所造成的结果也是法所接受的,将其与不法侵害结束后的行为以及过当的结果搅合在一起,“将后面的事后防卫的违法性对前面的正当防卫行为进行反向覆盖”,合法跳进了非法的染缸,这显然对防卫人不利。为消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日本学者提出,“在侵害当时的第一暴力与侵害结束之后的第二暴力能认定存在主观上的连续性、客观上的行为样态的连续性的场合,就可以将整体行为评价为一系列的防卫行为,对于整体行为认定成立防卫过当。不过,如果整体性评价二者,反而会在处断刑上造成行为人之不利的,就可以分离二者,就第二暴力认定成立完全的犯罪(实际限于那些由第一暴力引起了重大结果的案件)”。也就是说,在第一暴力造成重大结果仍属于正当防卫的情况下,即使第二暴力存在着时间过当,也不再做过当的认定,直接认定第二暴力是“完全的犯罪”。这种观点带来了时间过当认定的不确定性,并非妥当。
本文主张,通过整体性判断在确定了行为的防卫性质以后,对防卫行为造成的后果应作分别判断。即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防卫行为造成的后果(在我国刑法中应该是指“重大损害”)是由前行为还是由后行为造成的,换句话说,整体性评价仅限于前后行为防卫性质的判断,将不法侵害结束之后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肯定其防卫性质,至于防卫行为造成“重大损害” 结果的归属,只要前后行为是可分的,就应该将前后行为加以分开,就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分别评价的立场。如此,就可以既不影响整体的时间过当认定,又可能将符合正当防卫要求的前行为以及结果阻止在防卫过当评价范围之外,有效避免整体性评价可能给防卫人带来的不利后果。
如前所述,在我国,防卫过当是指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如何认定防卫过当,理论上存在着一体说和分立说之争。一体说强调:“只是在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存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不存在所谓‘手段过当’而‘结果不过当’或者相反的情形。”“若防卫行为没有造成重大损害,便不宜认定其‘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此时仍应肯定防卫人构成正当防卫。”分立说认为,立法机关设定的防卫过当条件中,一是强调超过必要限度的明显性,二是造成重大损害。理论上可归纳为行为过当和结果过当,并且只有在两者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本文认为,一体说常常导致“唯结果论”,只要发生了重大损害,就可以推定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未必对防卫人有利。分立说防卫过当的成立而言,多了一个排除性选项,符合立法的初衷,有利于防卫人正当防卫的认定。以分立说作为理论基础,时间过当只是肯定了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但并非一定就该当了防卫过当,关键要看是否造成重大损害。结合我国刑法正当防卫制度的具体规定,时间过当可根据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1.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时间过当行为,但过当行为并未对不法侵害人形成重大损害,不符合防卫过当的构成要件,防卫人无需对过当的防卫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其中又包括三种情况:
(1)时间过当行为没有造成任何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结果。例如,前例“昆山反杀案”中,防卫人于海明的最后两次砍击在本文看来可以评价为时间过当,但根据过当结果单独评价的原则,这两次砍击由于没有击中刘某,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则不构成防卫过当,于海明不需要为时间过当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2)时间过当行为造成了轻伤的结果。由于轻伤的结果并非重大损害,因而不能成立防卫过当。有观点认为:“超过时间限度的防卫行为造成了非重大的普通损害的(如轻伤害),也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而不应认定为量的防卫过当。”但依据分立说,时间过当的认定与防卫过当的成立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时间过当首先确定的是防卫行为逾越了防卫的时间界限,即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在这基础上还需要分析该过当行为是否造成了重大损害。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如只是造成轻伤,并没有该当刑法上的防卫过当,不需要承担防卫过当带来的刑事责任。不过,既然行为已经超过了时间限度,则时间过当已经形成,轻伤的后果是由时间过当行为造成的,仍成立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并不必然免除民事责任。
(3)尽管发生了重大损害的结果,但该结果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实施的防卫行为造成,时间过当行为与重大损害没有因果关系。例如,被害人张某酒后到被告人王某经营的饭店打砸玻璃及有关物品,王某闻讯后赶到,与张某相互撕扯并相互拳击,后王某用双手用力将张某推倒,致张某后枕部撞击地面,王某见张某欲爬起来,又用木棍击打到张某的头部。张某送医院不治身亡。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害人死亡原因系王某双手用力将张某推倒致后枕部撞击地面造成重度颅脑损伤所致,而王某用木棍击打的不适时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法院据此审理后认为,王某一开始针对张某的不法侵害,用双手将张某的推倒,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王某用木棍击打张某的行为属于防卫不适时,但不适时的防卫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如果是正确的,则法院的分析思路基本是正确的,本案被告人王某用木棍击打张某的行为可以评价为时间过当行为,但死亡结果却是由强度过当所造成,时间过当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王某不需要就时间过当承担刑事责任。
2.如果重大损害是时间过当行为所造成,则该行为符合防卫过当的构成,应该根据刑法防卫过当的规定处罚。例如,女青年李某上山砍柴时遇到同村的张某,张某顿时起了淫心,要求与李某发生关系,遭拒绝后,张某拔出水果刀进行威胁,并强行奸淫了李某。强行奸淫行为实施完毕后,张某穿裤子时,李某用柴刀朝张某头部连砍两刀致其重伤,然后急忙逃走。对李某的行为应该如何处理?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强奸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李某遭受性侵害的后果亦已形成,行使正当防卫权的条件已经丧失,防卫人的行为应当属于事后加害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李某的行为应属于正当防卫。张某在穿裤子时,无论是从时间范围还是空间范围,都对被害人李某有紧迫的法益侵害的危险性的征表,李某只要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张某可能再次实施强奸行为或更严重的人身伤害行为,就应当认定为危险状态的持续从而可以实施正当防卫。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偏颇。尽管按照传统事后防卫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能够成立的,但女青年受侵害后处在激愤之中,在侵害现场的趁势反击行为直接以故意杀人罪处理,明显存在着不合情理之处。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在穿裤子时,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因为张某对被害人李某有紧迫的法益侵害的危险性的征表。这种观点将正当防卫需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置换为“有紧迫的法益侵害的危险性的征表”,脱离了刑法防卫需要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规定。如果将李某行为评价为时间过当,则可能合理得多。虽然强奸行为结束,但张某是否连带实施新的侵害行为仍处在不确定状态(毕竟强奸后杀人灭口以及抢劫等连带性的犯罪也不鲜见),又是在侵害的现场,其砍击行为应作为时间过当认定,由于造成了重伤后果,应成立防卫过当,李某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应予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在防卫行为致不法侵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致伤或者致死的结果是在不法侵害结束前还是结束后的防卫行为造成的,应秉承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如甲欲伤害乙,持刀对乙的实施不法侵害,乙在反击的过程中夺刀反刺了甲一刀,甲踉跄挣扎时,乙几乎在相同的部位又捅了一刀,致甲重伤。后面一刀可以作时间过当评价。经司法鉴定,两刀中只有其中一刀是刺中要害的致甲重伤的。如果能够认定甲的重伤是在不法侵害进行过程中的防卫行为形成的,则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如果认定甲的重伤是第二刀即不法侵害结束后形成的,则是防卫过当,但如果无法确定,应如何处理?理论上一般认为,在无法确定是哪一个行为造成结果发生的情形下,本着事实认定应秉承“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宜作防卫过当的认定,而认定结果是在正当防卫过程中形成的。不过,日本刑法学界也有观点对此质疑认为,在检察官无法举证是哪个阶段的暴行导致了严重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 的原则,按照“正当防卫行为”导致严重结果的发生来处理,因而就没有了对于严重结果承担刑责的余地,从而缺乏妥当性。本文认为,在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中,“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当予以坚持。既然无法肯定是正当防卫还是时间过当中造成了不法侵害者重伤的结果,就应推定该结果是在正当防卫中形成的,而不能将相关的结果归属于时间过当行为。
4.特殊防卫并不必然排除时间过当。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有颇具特色的特殊防卫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特殊防卫案件,排除了强度过当,但是否存在时间过当情况?有观点认为,“在被害人被行为人最初的正当防卫(第一次反击)制服之后,已无恢复原状、再次发起攻击的可能,但行为人因为被害人的紧急不法侵害而‘精神高度紧张,心理极度恐惧’,辨认、控制其行为的能力降低,对被害人的情况浑然不识,仍然继续进行反击(第二次反击),导致被害人死伤的场合,行为人的继续反击行为可以认定为刑法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特殊防卫”。此种观点并不妥当。因为正当防卫是违法阻却事由,而“精神高度紧张,心理极度恐惧”充其量是责任阻却事由,阻却事由的性质不同。在本文看来,如果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正在进行,防卫人行使特殊防卫权,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但特殊防卫并不必然排除时间过当。在防卫人的防卫行为产生防卫的效果或者不法侵害人已经逃避的情况下,防卫人继续反击的行为并不当然排除时间过当的成立。例如,被害人李某酒后无故滋事,在宿舍门口遇到从外面回宿舍的被告人白某,李某右手持单刃匕首两次刺入白某右侧胸部(后经鉴定白某的损伤构成轻伤二级),白某在夺匕首的过程中将李某拽倒、自己也摔倒在地并从李某背后抱住李某,将李某右手中的匕首夺下后,用左手持该匕首刺入李某左侧颈部,并用力划了一下,后李某抢救无效死亡。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起诉,辩护人认为应成立正当防卫。法院审理后裁判认为,案发时本案被告人白某面对正在进行的危害自身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即被害人李某持匕首对其胸部连刺两刀的情况下,具有防卫的紧迫性,白某夺匕首以及和李某扭打的行为都基于防卫的目的,属于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但白某在把李某拽倒在地,面朝李某的背部,并已经把匕首夺过来了的情况下,侵害人行为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且无证据证明侵害人会继续暴力伤害,白某感觉自己活不了,随即向侵害人暴露的左颈部捅了一刀,并用力划了一下,造成被害人大量失血死亡的严重后果,已经超出了防卫的限度,也不宜认定为特殊防卫,应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据防卫过当的规定,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此案中,尽管被告人一开始的防卫行为存在着特殊防卫的基础,但当不法侵害人已经被制服的情况下,其继续实施的反击行为是过当的行为,应作为时间过当认定,法院将被告人逾越时间界限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是合适的。
时间过当概念,独特的问题解决路径,既维护了传统正当防卫的时间性条件,又有效平抑了防卫时间的精确性与防卫人难于把握性之间的紧张,理论上不难证立。然而,缺乏司法解释和判例的明确支持,人们一开始总是本能地排斥新的解决方案,宁愿选择在传统理论的框架内牵强附会地修修补补,而对个案中防卫时间把握宽严失度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但正如法益、客观归责等概念已经成为实务中一些疑难案件的分析工具一样,时间过当概念展现了向防卫人适当倾斜的刑事政策以及兼顾侵害人利益的公正性,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被理论界普遍认同并成为我国实务界处理防卫案件的重要分析工具。声明:本网部分内容系编辑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
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本站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应用建议。本站拥有对此声明的最终解释权。
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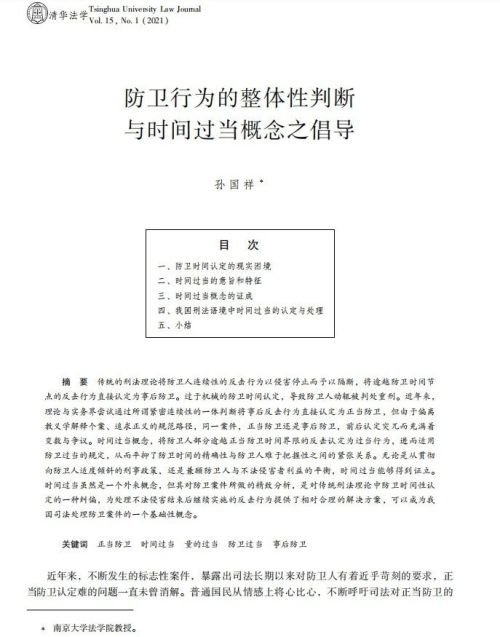


发表评论